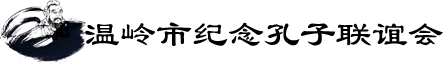论民主仁学
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冯友兰。他在最后一部著作──七卷本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之第七册中分立专章,称熊十力的哲学体系为“中国哲学近代化时代中的心学”(或曰“新心学”),而自称其哲学体系为“中国哲学近代化时代中的理学”或曰“新理学”,并自称是“接着讲”而非“照着讲”理学的。但冯氏的“接着讲”,是用西方逻辑学的方法讲宋明理学的旧概念,诸如无极、太极、理、气、心、性、道体、大全等等,其结果,无非是“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”,在理论系统上并没有大的突破,而对宋明理学及冯友兰“新理学”本身的人文精神的阐释反而显得苍白无力。但冯友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仍是有所贡献的。其贡献首先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“精神境界”说。他在《新原人》中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四个层次,而以“天地境界”为最高境界。而所谓“天地境界”,就是“自同于大全” 的“仁”的境界。他在论述“天地境界”时指出 :“这种精神境界叫做‘仁’;行‘仁’的下手处,就是‘忠恕之道’。‘仁’是儒家所说的最高精神境界的名称。……它可以是指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德之一,也可以是指最高精神境界。”13再进一步 ,冯友兰十分明确地把“ 圣贤 ”当作是一种境界 ,指出“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圣贤,都是指人的精神境界而言”14。其次,冯友兰尖锐地批判了违背人性、违反辩证法的所谓“仇必仇到底”的“斗争哲学”,而创造性地阐释了宋明理学家张载的“仇必和而解”的哲学命题,认为这才是“客观的辩证法”,并断言:无论是现代社会、现代历史还是“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”,都是“向着‘仇必和而解’这个方向发展的”15。
总之,从维新仁学到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理论,都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分崩离析、中国社会急需现代化、传统儒学面对西学、新学的严重挑战并受到全面批判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论重建工作的,这个时代背景也决定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是应对型的,而从康有为到牟宗三这些儒学大师,他们虽然学兼中西,但对中国现代化仍然存在许多误解与迷惘,所以在其新儒学理论体系中必然存在种种的矛盾与窒碍。或许可以说,所谓“现代新儒学”虽然已形成为带有国际性的新思潮,但这一思潮仍然只限于在少数学者或所谓“知识精英”中研讨流行,仍然只是学者书斋里或大学讲坛上的学问,还没有成为真正能引导社会、掌握民众的强大精神力量。四、新世纪的儒学展望:民主仁学之我见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,是中国与世界发生巨变的时期。从世界范围而言,现代科技文明取得了日新月异的长足进步,将世界带入了以信息化、电脑化、网络化为标志的“知识经济”时代,并出现了经济发展上的市场化与全球化、政治关系上一极独强下的多极化、文化上互相融通的多元化、价值观念上求同存异的趋同化的新趋势。市场经济以及人权、民主、法治、科学等价值观念与实用制度,已经不再是西方的“专利”,而成为全人类所能共享的资源了。从亚洲而言,日本与欧洲“四小龙”在本世纪后半叶开始经济起飞,到世纪末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,而形成了与欧美现代化模式风格迥异的“东亚模式”,印度与中国正在崛起而受世界瞩目。就中国而言,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,开始摆脱“不断革命”论教条的束缚,而进入了以“实事求是”为思想路线、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、以 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”、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期,
并且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和思想文化的空前宽松局面。这给予人们的启示是:世界各国、各地区的基本目标虽然都是要求社会的全面现代化,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唯一的 ,而是万殊的 ,它可以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特色的情况下接纳现代科技文明、社会文明与精神文明,实现经济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现代化。可以断言,在二十世纪末所出现的经济、政治和文化趋势在新的二十一世纪将会继续发展乃至强化。但全世界更愿意看到的新世纪的前景 , 决不是一个美国世纪 、欧洲世纪或中国世纪 ,而是一个没有战争、没有恃强凌弱、没有贫困的和平、和谐、民主、富足、文明的新世界。这也是儒家与东西方一切期待真善美境界的哲学、宗教的美好理想。
处在这个大趋势下,在本世纪初、中叶受到严酷冲击,批判而一度“花果飘零”、衰极一时的儒学,到世纪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、复兴的良机。现化新儒学从对古典儒学与现代西学的反思、回应中基本上完成了从被动到自觉的改良与转型,于是一面形成了从陆王心学与康德哲学中“转出”并糅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牟宗三的“道德的形上学”(实即“新心学”),另一面则形成了综合程朱理学和西方逻辑学、知识论而“接着讲”儒学的冯友兰的“新理学”。今天,凡是关心中国思想发展动态的人,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,恐怕都不得不承认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存在与复兴(指形成一股思潮)已经不是是否可能而是已经成为事实了,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这一事实并思考其发展方向而已。
那么,新世纪的儒学形态是否继续是牟氏“新心学”或冯氏“新理学”的延续、放大或完善呢?换言之,新世纪的儒学新形态是否必须在“新心学”或“新理学”中择其一而从之呢?我的回答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,而是:“唯唯,否否,不然!”“唯唯”者,唯其真理而从之也。“新心学”或“新理学”虽各得一偏之真理,也是应当而且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的,所以它们在新世纪不会死亡,而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与价值。否否者,否其所当否,即批判其时代局限和理论缺陷,以使当代新儒学的理论重建建立在更加适合时代的需要、更加理性化的基础上。不然者,不以“二者必择其一”为然也。
5/17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|